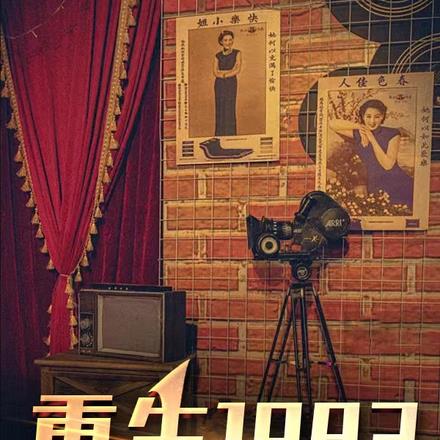两个走向永恒之邦的过客 20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6.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奥克塔夫·皮尔麦茨的死仿佛跟任何一个人的死一样平淡无奇。几个月以来,他感到气闷,腰痛,腿部水肿。一八八三年二月份,他请来了村子里的本堂神甫听他的忏悔,并且要求家里全体仆役原谅他对待他们不够耐心。他年轻的侄女们决定念一次九日经为他祈福。病情随后有所好转;到了四月末,他甚至康复到可以接待客人。一天晚上他迟迟未睡,要给园丁几个命令,接下来的夜里,病情突然恶化:“我不行了,就要死了。永别了,埃米尔。饶恕我,上帝!对不起了,母亲!”他死得像个乖孩子,永远保持着他本性中的某些方面。
伊雷内夫人记录了这些细节,为比利时失去了这位作家表示惋惜,“他发挥了他的天才,就是为了给上帝争得荣誉”。她指出,她儿子奥克塔夫的作品,除了《树丛》和《致约瑟的书简》之外,书名都是由她选择的,这样一来,有三个书名就都是她起的了,而这并不要求多么大的发明创造。她其实是想特别说明,一直到最后,她都给她的儿子提出告诫和建议。她说,她并不想在这个儿子死后再活很长的时间。然而有关死亡的事,人们总是估计错误。她又活了很久。不仅死在奥克塔夫后面,而且在第二年死的埃米尔以及她的小妹妹佐埃的后面。德里雍家的最后一位小姐的晚景凄凉。一八九四年,我的母亲曾经毕恭毕敬地对这位频遭丧子之痛的姨姥姥做过一次短暂的拜访。
奥克塔夫的临终这样不事张扬,仿佛不该给各种传言以口实。然而,就像每个诗人的死总会引发的那样,传言还是越来越多。其中一个说法浪漫得出奇,让人忍俊不禁,甚至被写进了书里:奥克塔夫在一个美丽的月夜,独自一人在树林里拉小提琴,受了风寒。但这也是唯一一个有部分事实基础的传闻。自从音乐在中学的忧郁气氛中给了他安慰后,就成了他最喜爱的一件事,就好像他弟弟一样。而且,他喜欢把音乐跟森林中的天籁与芬芳混合在一起。他的一封信里曾写道,他每天晚上到树林中间去,用他珍贵的瓜尔内里提琴演奏一首门德尔松的奏鸣曲。他又接着说,很久以来,他就给这种愉悦画上休止符号了。但伊雷内夫人写道,在她儿子去世以前的几天,看到他冒着四月晚上的潮气,拿着他的提琴留连在外迟迟不归,心里很不安。人们也知道,村子里几个微不足道的流浪乐手,玩手摇风琴的,在大路上用吉他一曲接一曲地弹奏那不勒斯小调儿的孩子,他都请到城堡里来,那些人还把他称呼为“少爷”。他也很乐意屏定声息,藏在小树林后面听他们海侃,那些贝克福尔地方路易二世时代的奇谈怪论显然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还有另外的一些毫无根据的传言,说他挨过一个流浪汉或是偷猎者的冷枪。这当然是因为他总带着一支卡宾枪在夜里独自闲逛,而且大家都知道他轻易地接待一些闲人,施舍得也过于大方,特别是因为歹徒在整个乡间肆虐,引起了普遍的惊慌甚至恐惧。最后,人们压低声音,说到跟当年让雷莫丧命相似的一件事故,说的是这个散步的人不懂如何把枪装上子弹。关于那个年轻人的死亡,家人怀着虔诚的善意说了许多谎话,无怪乎荒诞不经的传言会那么多。这里还夹杂进来一个诗意的想象角落:大家一致认为或许导致诗人死亡的那个事故是在深夜的某个时刻发生的,就在这个对他来说十分神圣的树林里,他在许多地方的树干上,刻上了这样的文字:NOX-LUX-PAX-AMOR。显然这就是他在森林的梦幻中不断重复出现的主题。
伊雷内的笔记和病人亲笔的信件写得都很清楚,不仅如此,如果需要的话,奥克塔夫的本性就没有自杀的倾向。这个题目,他自然涉及过。他觉得某些人适合于自觉自愿地死亡,在这些人里肯定就有雷莫,对生活有正面的炽热精神,他的本性不能容纳这过于充溢的力量。再加上基督教的精神把他推向了这个出口。我们很清楚,所有人,哪怕比奥克塔夫更为坚强,也会很容易地作出他本不赞成或他的信仰不容许的事,至少让他有一闪之间的错念,昏昏然不能自持。死亡的欲念也许是他的一个“黑夜中的暗斑”。他有这样的特性,二十岁时,他就为已不是十二岁而惋惜;到了四十四岁,他说他不再为莫里斯·德·盖兰的早夭感到痛惜,他一直热诚地崇拜这位诗人的作品。“他死得好,不然的话到今天就得活到六十六岁了。”五十岁时,他一方面惧怕死亡,同时又觉得活着太疲惫,在两者之间摇晃不定。他向往着让他本身的一部分从时间当中脱离出去,时间是“汹涌澎湃的海洋,上面漂浮着皮囊形体”。在这种情况下,时常就像一个疲乏不堪的人自做主张,作出了精神理智不敢作的决定。奥克塔夫对生死的理解就停留在这个生理乃至炼丹术的水平上,就好像人站在自身以外,不自觉地旁观着一个他自己引起的分化瓦解的过程。任何暴力的动作,任何情节剧中的小插曲都不需要。“改变形态是再自然不过的事。”用不着庄稼汉在瓜尔内里小提琴上狠狠打一拳或是不小心在枪里装上子弹。
乍一看,他的日子过得并不辉煌灿烂,倒有些轻佻放纵,然而却花尽了他的力气。无论在大事还是在小事上,他对他的家里人,外省的大资产阶级社交圈子,以及他始终遵从的高雅原则都作了让步,而有时候他也用跟他弟弟一样尖刻的语言去谴责外省的富户颟顸昏聩。在另外的方面,他同样表现出弱者怠惰性格的强大威力。他的父母,后来是他孀居的母亲大概曾经梦想着他在学业上精进不懈,一直上到大学。而他却没有这样做。接下来,他也完全可以从事一个有家学渊源的,在他看来也相当体面的职业,出人头地(“我一点也不经营我的土地,我不到任何别的地方去住,我紧紧地攀住我自己的山顶”)。在婚姻上他也同样。这个浪荡子承认,他的舞跳得很平常,也不会说俏皮话讨年轻姑娘的欢喜,他拿眼前的表兄弟阿尔蒂尔作他的榜样,阿尔蒂尔很长时期对夫妇之间的欢娱裹足不前,到最后才娶了表妹玛蒂尔德,一位出自名门的可人淑女。后来,埃米尔跟一个参议员的女儿结了婚,让伊雷内夫人心满意足(“这是我一生中最美的一天。”),也让她希望奥克塔夫学习这个好榜样。但她的希望落空了。当时的重重规矩把这件事反倒弄得复杂化了。奥克塔夫对一个思想很正统的老伙计承认,他跟“一个金发女郎”保持着恋情。那个规矩正经的伙计暴跳如雷,要求他如不斩断联系就立时把她娶过来。这两条道路大概他都没有考虑过。在这个道貌岸然的社会圈子里,心灵和情感上任何一点微妙曲折都没有立足之地。
他的幼弟,“那个可怜的孩子”在理智上迷失了方向,显然引起了家里人无休无止的争论,仔细阅读奥克塔夫的作品,就可以发现这些争论的痕迹。如今我们觉得,他有关雷莫的那本书出言过于谨慎,是个瑕疵。说到书中主角的最后一刻时,又用十分笨拙的语言来掩饰真实,简直成了败笔。据说奥克塔夫希望读者自会识破其中奥秘。压在奥克塔夫身上的禁令和忌讳一定是过于沉重,直到一九五二年,一位给诗人写传记的循规蹈矩的作者还推敲字句,用模棱两可的文辞来描写费尔南-雷莫,说他“在追逐他自己也弄不清的海市蜃楼”,一点也没有提起他的自由主义、和平主义和实证主义思想,同时也瞒过了他成了家里人中的异端所引起的悲剧。就是这位传记作者对那本“小说”弃之不顾,那是唯一一部以他弟弟的信件为素材的作品,在里面奥克塔夫总算鼓起勇气,稍稍正面地对待真实。这样的安排并不令人惊奇:写传记的人时常这样对事实的本质避而不谈,或者不动声色地抹杀掉。起初,奥克塔夫出版了他的那本小小的书,只印了十册,也没有署名。接着,某些人很赞赏,他得到了鼓舞,又出了一百册,同样也是匿名的。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在这布满地雷的地域中他已经走了很远。要出版这部小心翼翼的作品需要一些勇气。
奥克塔夫·皮尔麦茨曾说过:“有些人在奇特的、不能实现的愿望中耗尽了自己的生命。一种希望,不管多么不合常情,也都像情人似的,让人难以割舍。”这种以真实为目的的追求不可能实现,向他预示着结果是个悲剧,在他的思想里,这条路显然就是雷莫所走的;而对于美的追求,他觉得更像是他自己的探索。雷莫的朝圣之旅很快地就走上了年轻的希格弗里德的巡游之路,这个英雄曾擎着火把沿着森林中的小路去探险;而他的朝圣却成了一首悲壮的交响乐,缓缓地告终。在他个人的忧郁中再加上世界的痛苦这个让人不能忍受的重量,只有他对自己具备作家能力的信任才在某种程度上减轻其痛苦的程度。于是,他用严格的洞察力来剖析自己,早在一八六七年,他在给邦塞的一封信里就说:“我在这里承认,我一点天才都没有。我愚鲁笨拙。我从我身旁的人汲取思想。我背负着传统蹒跚而行,能够真切地说明我内心世界的语言还有待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灰心丧气的迹象不但没有减少,反倒增加了。他并非不了解,他本属于圣伯夫说过的那种缺乏天才的种族。他走到了他描写过的那条死胡同,在这个时候,这个囚徒在牛角尖里把自己憋死。
布鲁塞尔的各家报纸用尊敬的口吻宣布了他死亡的消息。《舆论回声报》简单明了地说:“他是一位有成就的作家。”《布鲁塞尔新闻报》的口气更为明晰谦和:“我们的作家不多,他是其中一个。”地方性的报纸谈论得更热烈,连篇累牍地说到他“出身于本地区最高贵最受人尊敬的人家”,“有一位尊贵的,德高望重的母亲”,“有相应身份的本堂神甫为这个英年早逝和蔼可亲的作家主持了丧仪”,“贵族和神职人员中的头面人物和本区的老百姓”也参加了典礼。有人还告诉我们,村子里的合唱团还在这个业余音乐家的葬礼上唱了歌。一直到最后一刻,他还是这个家的儿子,是个永远的年轻人,乐善好施的财主。当地的慈善机构为失去了他而感到痛惜。各篇悼词在宣读之前都经过丧家的筛选,怕的是悼词中把“可怜的奥克塔夫归入自然神论者,甚至唯物主义者之列”。
他埋在一座崩塌为废墟的古老教堂的祭坛底下,就在雷莫旁边。当年他曾由伊雷内夫人帮着,把那教堂改建成家族的墓地教堂,免得被彻底拆毁。一九二一年,雷火把房顶烧毁了,但那房子夹在村子里的新楼之间,仍然存在。这里已完全不是最初那充满浪漫气息的建筑,当年兄弟俩曾在这里掩起书本,抬起眼睛眺望着园子里的郁郁林木,心里想着,有一天他们会在那里安息。
在这里,我转录了奥克塔夫的“虔诚的回忆卡”,就好像诗人本身在他的《雷莫》一书中转录了歌德的讣闻似的。那是他那还在上大学的弟弟从属于上流社会的一位魏玛老妇人手里得来的。但这一次,我并不像奥克塔夫当年对《浮士德》的作者一样,把荣耀与死亡相比。这区区的几行字表明了,一旦入了土,一个人的独特面貌是多么迅速地消失净尽。
<blockquote>
死在天主怀中的人是有福的。
虔诚地怀念
奥克塔夫-路易-邦雅曼·皮尔麦茨先生,
他在一八八三年五月一日于阿克兹城堡去世,
享年五十一岁,
举行过了神圣的临终圣事。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
(《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十二节)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约伯记》第十九章)
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
(《箴言》第三十一章)
我只为自己要求一件事:你们在祈祷时,回忆起我。
(圣奥古斯丁)
圣母马利亚温暖的胸怀,是我的栖身之地。
(百日的赦罪)
慈悲的耶稣,给他永恒的安息。
(七年的赦罪)
</blockquote>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奥克塔夫晚年曾说过,他只能在祈祷中找到一片绿洲,然而在他的作品中却只有两次提到耶稣。在《雷莫》一书中他指出,他那个时候的人在睡梦里可能要求《福音书》给以帮助;但在别处,他用更为动人的方式提起耶稣在拉撒路坟墓前的眼泪。圣约翰的这篇福音,文辞如此华美动人,顺理成章地代替了人们在前面看到的到处风行的说法。显然,任何人也没有想到这一点,或者说,人们更喜欢习惯引用的那些平凡无误的章节。在这方面,他最喜爱的圣者,阿西西的圣方济各也作不出什么贡献。
但是,为这个值得追忆的人物所选择的形象并非毫无动人之处。在这宗教风格的文字中,就在那时,也微微散发出十七世纪那庄严的气氛,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圣约翰的形象,披着长长的卷发,穿着高贵的粗毛衣服,用一只圣杯来接从耶稣的双脚滴下来的血。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人们只能看到下半部。这幅雕版画也许会让他高兴,他也尽力用同样的方法来接住雷莫的血。
<hr/><ol><li>✑拉丁文,黑夜-光明-平和-爱。​</li><li>✑Maurice de Guerin(1810-1839),法国浪漫派诗人。​</li><li>✑德国民间史诗《尼伯龙根之歌》的主角。​</li><li>✑《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中说,耶稣在拉撒路的坟前,看到他的姊妹和朋友哭泣,也流出了眼泪,耶稣终于使拉撒路复活,从坟墓中走了出来。​</li><li>✑Saint Francis of Assisi(1181或1182-1226),天主教方济各会和方济各修会的创始者。​</li></ol>